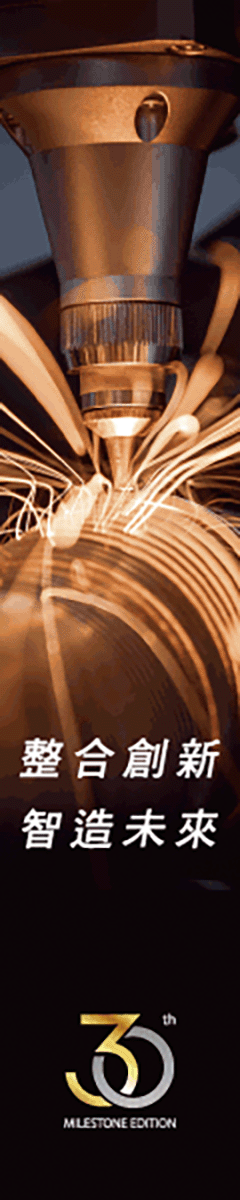今天晚上,踏进了一个村子。每走一步,时光好像不断向后退去。
这个村子,位于车水马龙的福和桥边,但一拐个弯,弯进了村子里,台北城的喧嚣尽皆褪去,替代的,是原该只属于乡间的那份恬静。更吊诡地是,这座山城的矮房大多简陋残破,多数住户也已离开,但却搬进了一群新人类,他们就在这陈旧的破瓦石墙中,找到了在创作上源源不绝的支撑力量。
这个大隐隐于市的山城,即是公馆后山上的「宝藏岩」聚落,过去是一群老兵的违建住所,如今则成了许多文创工作者进驻的艺术村。这些人有的创作动画、有的做手工艺,有人在搞剧场,更有人跑到这里来卖咖啡。
卖咖啡也能算是文创工作吗?当然算。今晚走进的这间「尖蚪」咖啡,在小小两层楼的空间内,各式古早味的纱门、桌椅、沙发、书架、相框等各安其位,每个转角都摆放着回忆、伴随了惊喜。你可以点杯咖啡,随手取得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籍、杂志,让身心沈腻在浓浓的自在中。
这间店的老板,无疑是装置艺术的工作者,更是美食、气氛、生活的经营家。
来到这里,不仅让我想起二十年前,学生时期经常流连的那家店。它也位在公馆区,靠近耕莘文教院,店名叫做「甜蜜蜜」。它不只卖咖啡,还卖「个性」。
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!
老板吴忠炜是一个道地道地的怪咖,一身邋遢的穿著,活像一个街头游民。但他却以尊荣的素人艺术家自居,顶下这家店,只为了将整个空间塑造成自己的一个作品。里头的摆设都是他「拾荒」再加工而来的成果,例如,一进门就是一扇大大的拱形木窗被当作屏风,听说是来自废弃的台北古城门墙。
印象更深的,则是店里的那间厕所,浴缸中塞满了他捡拾回来的坏掉玩具。如厕时,一个和真娃娃一般的玩偶就坐在玩具堆上,瞪大着眼睛和你对望着,还真是毛毛的有趣!
想当然尔,这里就成了一众同样怪咖的人士聚集之地。有人搞乐团、剧团,有人拍实验电影,更少不了一些异议份子,为同性恋、「还我土地」等议题而纠众走上街头。
还记得有几天,在店里都没见到忠炜,却在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相遇。
那个时候,新生南路一带的日式房子面临逐一被拆除的命运,我和朋友偶而会翻越已拉縄封锁的老房子外墙,在倾圮、杂草丛生的屋中寻宝。
那一天,居然让我们寻到了这位仁兄,我们彼此都被吓到。在他身边的地上迭了不少方便面空碗,看来已在这屋中待了一阵子了。问他在这里干什么,他只是笑笑的说:「思考」。
一个人躲到一间空屋中「思考」,还真像他会做出来的事。
再将场景转一转,1970年代的美国,或许更为狂热。游行、摇滚乐、迷幻药、禅学充斥校园,一股追求心灵觉醒的次文化在这群青年的心中炽烈地焚烧着。学生时代的贾伯斯,恭逢其会,他浸身其间,吃素、修禅、打坐,也吸食迷幻药。而这些,让他练就一身凭「直觉」去设计产品的独特能耐,更成了他一生「忠于自己」的勇气来源。
看来,在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地方,总是不断地有一群人-通常是年轻人,大胆且真诚、热切地想要为自己、为世界做些什么。他们不吃老爹、老师或权威人士的那一套,挂在口上的是:「妈的,没在怕的!」
40年很快过去,当年在车库搞PC的那群人很多已功成名就,如今另一群车库Hacker又在各地冒出。他们依然是爱搞怪的怪咖,但他们不再孤单的自己闷着头搞,而是透过网络串连在一起了。
这就是接替开放软件而起的开放硬件运动(也称Maker Movement),参与者各自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,集结成社群。本着开放精神,而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出更酷、更怪,或更好用的东西。
看起来,每个年代里都有黑客。当个黑客,不一定要有高深的技术,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愿被驯化的傻劲。然而,只有傻劲还是不够的,还要有支撑自己长远走下去的理念思考。
现在想想,忠炜的「思考」,与贾伯斯常做的「冥想」是同一件事吧,只是换了种仪式罢了。至于他们在思考什么、想通了什么,并非重点,重要的是他们想这么做,也去做了。
你呢,骇不骇呢?
(作者为CTIMES总编辑,本文刊登于CTIMES 248期,2012年6月号)